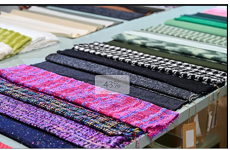马丁·瓦尔泽可有过笑的时候?或者干脆这么问——他有过年轻的时候吗?在他脸上寻找可能的笑容,就像在石缝里找掉在里边的花籽,也许能找到,但开花的把握是微乎其微的。
不高兴的人,满腹怨气的人,写出一本雄心勃勃的新作后不快地看着它落于读者手中的人,这就是瓦尔泽。他是一个联邦德国作家,1950年代曾是著名的文学团体“四七社”的一员,这个团体为更新德国文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泽三部曲”的作者、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就是从“四七社”走出来的最了不起的小说家,马丁·瓦尔泽与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等跟他都是同辈人,都生于1920年代,在他们进入成人期时赶上了纳粹德国最强盛的时期,然后经历了战争和败北。随后冷战开始,在1961年柏林墙建起时达到高潮,而这批作家都在此前夕,也即个人30岁左右的时候,拿出了最早的成熟之作:恩岑斯贝格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狼的辩护》,瓦尔泽写出了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而格拉斯正在专心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久后也将惊动世界,那就是《铁皮鼓》。
虽然《菲利普斯堡的婚事》和《铁皮鼓》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小说,但瓦尔泽和格拉斯的气质很有些相似,都可以说是易怒的、胸有怨气的人。《婚事》的主角,有个联邦德国最常见的男性人名——相当于“张三李四”的“汉斯”,他到斯图加特的一家报社应聘,一直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可以在经济起飞的西德活出个人样子,成为有家有业的中产阶级,但最后一场空。即便是喜欢此书的读者,也不容易对作家本人产生好感,因为瓦尔泽的语调很不友善,书中无论男女都得不到他的同情,汉斯的野心和他常常产生的愤懑、鄙夷、嫉妒、失落交织在一起,他在奚落别人的时候也被瓦尔泽所奚落。瓦尔泽在求学阶段,以一篇分析卡夫卡的论文获得学位,到了《婚事》时,他的确找到了些许像卡夫卡一样写作的感觉。
瓦尔泽的“火气”
批评家们对瓦尔泽是很挑剔的。瓦尔泽笔勤善写,作品不断,但他的主人公的性格都不可爱。1960年代他完成了一组三部曲作品,基本都算失败了,其中的第一部《半时》还厚达900多页,但无论批评家还是读者都不领会他的苦心。在戏剧创作里,瓦尔泽有所收获,1963年他完成了《房间之战》,这是一部反映家庭成员在言语中互相疏远为敌的作品,但是那年,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上演,不但占尽风光,而且主题也和《房间之战》高度相似。瓦尔泽只得把它压下,4年后才搬上戏剧舞台。
要到1978年的小说《惊马奔逃》出版,年逾半百的瓦尔泽才算停止了和批评家的纠缠。这则中篇小说依然沿袭他擅长的嘲讽风格,却有些出人意料地赢得了批评界和媒体的肯定,他被基本承认为战后德国的一线小说家,也能和比如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处于大致相当的水平。这时的联邦德国早已度过了所谓“经济奇迹”期,是资本主义西方“大家庭”里的一根牢固的支柱。这批作家都是在经济腾飞、国家上升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才华如何施展?瓦尔泽的火气又从何而来?
作家会注意被繁荣所麻痹和掩盖的东西。人们在繁荣中容易沉迷于当下,容易野心勃勃,无原则地附庸于国家政策和权威话语。作家们预见到,西德的经济成就被视为一种赎罪,昔日纳粹帝国发动了战争和屠杀,如今西德人得夹着尾巴做人,听命于美国的号令,为西方世界作出贡献,“不谈过去”是他们心照不宣的原则。瓦尔泽在这方面是做得最彻底的:他书写的人物,都是一些没有过去,也拒绝过去的人,他们把自己塞进当下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刻,每一秒钟,像《菲利普斯堡的婚事》里的汉斯,脑子里从没有闪过个人的过往,从没想过比如父母、童年之类平常人都会一转念想到的事。
记忆即虚构
在《婚事》发表前后,瓦尔泽还写有一篇随笔,主题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瓦尔泽深读过也很欣赏普鲁斯特,但他却总在做一件不容易讨人喜欢的事。普鲁斯特主张过去不仅应该而且可以书写,更主张“寻找失去的时间”。普鲁斯特创造的文体使读者产生幻念,觉得时间真的在字句间华丽丽奔流,瓦尔泽却说,用干燥的、夹杂了思辨术语的话讲,记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回忆出来的事全是当下的虚构。
在1966年出版的小说《独角兽》中,瓦尔泽写入了这样一段议论,他的比喻质地干硬,好用抽象词,危机风格的叙事让人想起了萨缪尔·贝克特:“显然,人体的各个部分都是存不住记忆的。只有心的暗处保持着一点点残余的光亮。但它也不含有任何记忆本身,仅仅是苍白枯干的种种事情,甚至只有它们的公式,公式想使一个过往的时刻复现于手中。可你看,公式也是徒劳。手就不是用来记忆的。”
即使是在后来的一部被认为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迸涌的流泉》(1998年出版)中,瓦尔泽同样嘲讽性地挖掉了“回忆”与“真实”之间的通道。普鲁斯特的叙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是从食物的气味、衣服的色彩、人的影子、踩踏楼板的声音牵出一整套绵延的往事,可瓦尔泽说,你要是想着依靠一些来自过去的东西的帮助,比如精心选择的段落,比如恰到好处的气息,或是其他感官或大脑信号,来唤醒过去,仿佛它就躺在自己身边那样,那是幻觉。你到头来会发现,你以为被重现的过去其实只是此刻你的情绪,你此刻的心血来潮。
瓦尔泽的这种理念并非只关乎文学理念。西德作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种愤嫉的认识,他们觉得西德是一个不真实的国家,它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有集体罪责需要承担。西德人的罪责感往往成为一个“美谈”,据说他们忏悔得积极而彻底,然而在作家的感受中,这意味着西德人的记忆是被设定了的,他们不能讲个人的体验,他们从出生(不管生于战前还是战后“婴儿潮”时期)开始就在奔向一种集体赎罪的命运。以此来看,瓦尔泽上述的理念,他对于“过去无法重现,重现则必为虚幻”的激烈断言,就有了一个苦涩的由来。他认为一个像他这样经历了整个纳粹政权上台到覆灭的西德人,是被取消了叙说往事的资格的人,也不能决定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
于是他们就成了如瓦尔泽所写的那样,徒然地、空洞地活在当下,他们目视前方,滋生欲望,心中一团乱麻。一个人至少得频频回顾自己走过的路,那是他立身的前提,是他寻求价值感的基础条件。当《惊马奔逃》里的赫尔穆特·哈尔姆意识到人生进入后半程,却没有积累下任何可供追忆、可供品鉴的过往,而只能又嫌恶又嫉妒地看向那些活得比自己更好的人时,他的面目可憎是可想而知的。
假如暗杀希特勒成功了……
对于批评家们来说,瓦尔泽最可诟病处之一,就是在小说里一向不提关于纳粹党、第三帝国的往事。他自己对此冷淡,也刻画冷淡这些往事的人物。但瓦尔泽的理由很充分:那种记忆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而再造过的,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否则就必须被压抑。正因此,他才会对维克托·克兰普热的日记如此看重。克兰普热生于1881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第三帝国存续的12年期间(1933~1945),他因为个人已有的社会地位加上种种幸运,没有被送进隔离点和集中营,因此见证了许多当时的事,并写下了详细的日记。战后,克兰普热生活在东德,又写下了战后的日记以及《第三帝国的语言》等著作。这些日记出版后,瓦尔泽盛赞克兰普热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读他的日记,终于可以想象德国完全可能走不同的道路,成为另一种样子。
德国的道路一定是通往奥斯维辛的吗?1960年代以来,瓦尔泽一直在卷入涉及这个问题的论争。他坚持认为未必如此。但是,他的坚持乃缘于他愤恨于一个事实,即德国人总是被要求忏悔,对从一战以来一直到奥斯维辛的建立,德国人应该持续悔过,不能把其中的任何事实解释为偶发。然而,克兰普热的日记给瓦尔泽的支持还是不够的,他又从另一位作者——约阿希姆·菲斯特的作品中找到了依据。菲斯特生于1926年,也是瓦尔泽的同龄人,他以写希特勒传记、研究第三帝国著称,瓦尔泽特别重视菲斯特写的抵抗运动史和“暗杀元首史”,他说,在那些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中,如有一次成功,则历史定将不同。
“我一次又一次按捺不住地想:这下希特勒肯定逃不掉了,然后战争就可以戛然而止,它的后果就会减轻很多”,瓦尔泽这样谈到他读菲斯特著作时的体会。他说,我们需要一种“事实性叙事”,我们需要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这样我们才不会陷入无望和狂热之中。“德国历史别无去向,必然要通往希特勒和奥斯维辛”——这是瓦尔泽不能接受的“社会共识”,它并非德国人心中自然形成的,它被强加给德国人,使其处在抬不起头的悔恨之下。
哲学上有个词叫“心象”,大致可理解为人心所形成的图像。心象必然要来自对外界事物的观看。在普鲁斯特那里,心象不仅鲜活,而且一个唤起另一个,形唤起声,声唤起影,彼此召唤,漫无穷尽;而在《惊马奔逃》中,主人公赫尔穆特·哈尔姆的心象则是死的,“假如他想记起什么,”瓦尔泽写道,“他就看到街道、广场、房间的一动不动的图像。一动不动。仿佛正值一场大难爆发,他脑中的心象都是了无生命的。这些图像比默片的剧照还显得静默。”有时他想要号令一声,让他认识的人列个队走过来。那些名字、面孔,一经唤起都会出现的。但它们出现在他眼前时,说是“如死一般”,那还太温柔、太客气了点。
西德人可以谈的往事,只能是经济繁荣语境下的往事,再往前的记忆是不能谈的,因为它有个统一的格式。这种被规范化的记忆造就了赫尔穆特的空虚。瓦尔泽用一种不无艰涩的笔法刻画赫尔穆特的精神困境:因为缺少可以滋润心灵的记忆,他深陷在中年人所有的种种烦恼、厌倦、焦虑、疲惫、衰败之中——它们构成了他全部的当下。有时,赫尔穆特来了情绪,把那些尸块一般的心象扶起来,拼粘它们,给它们上色、更衣,吹一口气企图让它们复活,再给它们增加文本描述……可是“他太老了,玩不了这种傀儡戏了”,要复活一件过去的事情,就像把一只无生命的木偶支棱起来,让它兴高采烈地活在观众的眼前。
一个“政治不正确”者
一个读者必须拿出十二分的耐心,才能欣赏瓦尔泽将抽象的东西具象化的方式。同时,他的第三人称书写总是保持着冷对人物的困境的姿态,他的声音是尖刻的,表情则离不开轻微的厌倦和郁郁寡欢。批评家总爱脱离文本审美,把作家拖入政治议论之中,而瓦尔泽对政治的抱怨总是出于一些极个人的理由,使人觉得他出言轻率,轻重不分。如在1977年,瓦尔泽谈到两德分裂时,曾发出这样的抱怨:我拒绝接受德国一分为二,西德和东德,两个都是民主国家,但是我身为德国公民,要去德累斯顿(位于东德)还需要得到东德的许可和签证。
这话激怒了威利·勃兰特,这位西德前总理曾因在华沙起义纪念碑前下跪的惊世举动为德国赢得了同情,并获得了1971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勃兰特当然代表了“进步”的方向,他抨击瓦尔泽是一个深陷于过去的人,心里只有自己的不方便:你不想想德国分裂的现实缘由是什么?你有什么理由非去德累斯顿不可?
读者们也不容易把赫尔穆特这样的人物放到“个人记忆遭到压抑”这种大的政治问题之下,从而对他产生同情。海因里希·伯尔是西德最善于描写社会问题的小说家,他的著名小说,如《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如《莱尼和他们》,都写了工人阶层的女性在经济繁荣期的受苦,既然社会生活要大踏步前进,那么没文化的草根阶层就得服从安排,在一个为中产利益服务的法律体系里沉默地活着。可是,赫尔穆特的精神危机却似乎是自找的,是性格问题导致的,他的感受力相当不错,人却乏味得很。
不过瓦尔泽正是靠着这本书成功的。西德文学批评界有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赖希-拉尼茨基,他在评论文章和文学节目中说的话,直接影响到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与风评,他认为,马丁·瓦尔泽的致命缺陷在于眼高手低,太想影响现实,但才华又不足以支撑雄心。《惊马奔逃》之后,赖希-拉尼茨基的评价有所缓和,似乎觉得瓦尔泽自己也平和了不少,懂得在个人的层面上表达那些纯属个人的烦恼,而不把它们的意义拔到不恰当的高度上。然而,瓦尔泽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小说《批评家之死》,用一种生硬的手法影射和嘲讽赖希-拉尼茨基,由于拉尼茨基是犹太人,而且是一个当年勉强逃离了集中营命运的犹太人,瓦尔泽的小说就涉嫌了反犹,这场越出了文化论争边界的公共事件,再次反映了他招人厌烦的个性。
“精神纵火犯”?
而在此之前,瓦尔泽早已造过一场更大的“轩然大波”。那是在1998年,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书业奖落到他头上,他准备了一份他早已知道一定会引起争议的演讲。演讲题目是他一贯的冷嘲热讽风格,叫“起草一份肥皂盒演讲的经验种种”。他在演讲中说,他的许多同行同辈,都在战后联邦德国的亲美国气氛中,压抑了自己对纳粹的同情心。瓦尔泽谴责这种自欺欺人。他说,德国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我们的罪责相遇,而他不想欣然接受这一“耻辱秀”,他宁愿别转脸去不看这种丑相。
他又讲,奥斯维辛一直是一根在手的道德棒子,何时想要敲打德国人,何时拿来就用。
演讲是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里发表的。这座教堂,在1848年革命后曾见证了德意志人首次谋划建立宪政民主国家的尝试(未成功),瓦尔泽的话音落下,观众们立刻起立鼓掌,足见瓦尔泽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不过随后,愤怒的责问就通过报纸——用今天的话讲——“持续发酵”了,大概有超过1000篇文章都在申斥瓦尔泽,说他讲话“过分了”,说他践踏了纪念的神圣意义。奥斯维辛既然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铭记它就意味着让这段历史永不再重演,可是瓦尔泽的话是那么的阴阳怪气,它的冒犯性使人无法忍受。
瓦尔泽的这番话,和1977年说关于去德累斯顿太麻烦的话,情况是相似的。它们都属于可以想,但不适合公开说的话,因为它们都转移了事情的“重点”。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埃利·威塞尔,这位集中营幸存者和大屠杀受害者的全球“代言人”,就一直关注着事关大屠杀、奥斯维辛、德国罪责的国际舆论的走向,尤其注意那些语言手段高超的公共知识分子,看他们是否在暗暗地“修正”历史定论。瓦尔泽的演讲一出,威塞尔立即正告他:你打开了一道危险的大门,使其他人得以闯入,从此以后,这些奉行完全不一样的政治观点的人,将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变得危险。
埃利·威塞尔的意思是,任何企图为纳粹时代招魂的人,都可以引瓦尔泽的话来给自己撑腰。他说得没错。公开说出话语,就如同把一件工具交给众人,瓦尔泽表达的是他的真实感受,可是其他人会把它用于不同的目的。心存纳粹思想的人拿到了瓦尔泽的话,将更加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被压制的不满。
很快,更大的责难来自德国的犹太人领袖伊格纳兹·布比斯,这位老者同样是大屠杀幸存者,也和瓦尔泽一样生于1927年。他的斥责简明扼要:瓦尔泽是个“精神纵火犯”,他传播了危险的想法。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德国人至少在表面上都接受罪责的传承,那么在此之后,他们将会主张自己的不满。这就是“纵火”这一比喻的意义所在。
布比斯逝世于1999年,但交锋的余波延及新世纪,涉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大有复现1890年代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时的盛况的感觉。时隔一个世纪,法国基本上再无重大的公共事件能激发起规模相当的公共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场转移到了已经统一的德国,在那里,一段从强国到战败的棘手历史,终于不能再成为“黑不提白不提”的陈年往事了。除了瓦尔泽,同样生于1927年的君特·格拉斯,在那几年里相继出版了小说《蟹行》、回忆录性质的小说《我的世纪》以及回忆往事的《剥洋葱》,每一本作品都掀起了一场舆论事件。《蟹行》讲了那些在父辈罪责的重压下逆反心理爆发,加入新纳粹分子、新反犹势力一边的德国青少年;至于《剥洋葱》,由于格拉斯透露了自己曾加入党卫队的事实,他也“求仁得仁”地被架到了火上。
格拉斯逝于2015年,8年后,恩岑斯贝格和马丁·瓦尔泽也先后故去。瓦尔泽一辈子少有招人待见的时候,恐怕日后也难有人发掘他的价值。他说过,自己就是个以思考和写作为职业的人,说了什么众人不爱听的也没办法。他的才华的确不足以捍卫他的脾气,可是在一个时代结束后,他那样的脾气也许是值得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