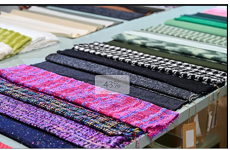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一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为已故之人作画,是太玄的门规。所以,饶是面前的小姑娘喋喋不休地说了几柱香的时间,他依然不为所动。
“太玄师父,小蝶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了,他也是实在饿了才会去偷点吃食的,何至于被活活打死?他不能就这么死了!太玄师父,骨儿从小没了双亲,孤苦伶仃的每月仍是虔诚信玄,从无二心。太玄师父连这点小小的心原都不能满足骨儿吗?”
他不动声色,笑了笑,执起石桌上的玉瓷茶杯,轻抿一口早已凉透的清茶,许久才淡淡开口,“施主,回吧。”
“太玄师父!”唤骨儿的小姑娘鼻子一酸,委屈得要掉下泪来。
说起与小蝶的相遇她眉飞色舞,讲到小蝶的死她面上凄凉,所有的解释哀求以及现在抛出家世博取同情,不过都为了这小蝶——他不知道他究竟是何方圣人,他只知道,门规既在,生不能违。
“这种事,何不问官去?”冷漠如霜的嗓音远远传来,执佛尘的玉女款款走上前,眉眼间更是冰冷,“师父见客从不逾三柱香,小施主,请回。”
太玄端着茶,再次抿了一口。真是苦得很,他想。
每日向他求画的人这样多,他不安排个专来逐客的门童,实在对不起自己。
小姑娘抿唇噤了声,许久才起身作揖拜别,“骨儿明日再来,太玄师父若不答应,骨儿便每日都来。”
太玄微微点了头,嘴角嗜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忽而执起手旁一枚黑子漫不经心地落于棋盘。
骨儿见状,自是知道无趣,一跺脚才愤愤离开了。
终于清寂下来。
他才恍然发现,桃树下的落花已积了薄薄的一层。
“阿宁,这步棋,走得可好?”他支起额,另一手拿了白子在石桌上轻轻点着,眉头舒了开来。
这盘棋,他一个人,已经对了三年。
“师父,以后不再见客便好。”玄玉女童一袭素衣,静静立他身后,良久才道。
她并不懂棋,他却总爱问她。末了无人应答,便自嘲地笑。
“不必了。”他将手中棋子掷回棋盒,似乎带着隐隐火气,“那小姑娘,她说要拜我为师,难保不是好事。”
玄道衰落,后继无人,这世间仍信玄的,怕是已经不多了。
二
丹青师作画,画成,画物即活。
太玄便是丹青师。
玄道有违天道,丹青师从来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却也是逆天而行。
太玄每日画些小物什聊以慰藉,安守本分。
然而,他却画出了玄玉女童息宁。
那日风云变幻,浓云如墨翻滚,他酒后执笔,醉眼朦胧中画像里便走出一个清冷如仙的女子。而后江山易主,天地换颜。他沉痛地扶了额,一个摇晃跌坐在太师椅上,近似呢喃地出声,“正当风息事宁,往后,你便唤息宁吧。”
钦天监急匆匆跑来告诉他,天呈异象,似有浩劫。
他这个国师,做得太累,也太不称职。他沉默良久,才低低开口对那徒儿说,“日后,你便跟着新皇帝吧。”
而后简单打点行装,离了京城,在山上做起了玄道大师。
自然,那个被他赋予了生命的女子,一直跟在他身边。
玉帝调查此事,他只道是世间凡人为权争斗,引起天象大乱而搪塞过去。殊不知是因为他在观里藏了个不该存在的人。
她本叫宁息,手法高妙的解画人。
被朝廷之事搅得心情烦躁,他借酒浇愁,随手画出的,便是她的样子。丹青师与解画人本为死敌,他虽深知,却仍是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
他义无反顾不畏前路的爱,最终让她死于非命。
“阿宁,你需知道,你只是个傀儡。”
“师父,我知道。”
所以,即使她已偷偷学他的棋技三年,也不敢有丝毫表现。
宁息擅棋,那日她在棋盘正中落下一子,素白的指还轻轻点在玉质黑子上,笑望着他。然后,便死了。
那盘棋摆了三年,她只落了一子。
解画即是破玄,遇上解画人,丹青师便没有活路。然而,死的却是她。
他与自己对弈,相思入骨,成疯成魔。
三
连着数月,雨势滂沱。
玄玉女童在他身前开道,推开观门时外头已立了个淋透了的小姑娘,抿着唇凄楚地望着他,“太玄师父,骨儿已等候多时了。”
“好生倔强的小丫头。”他扬起唇角,笑了。
“坏姐姐,为何把我关在门外?”骨儿抹了抹脸上雨水,闻声便委屈起来。
太玄转头看了看身旁为他撑着伞不动声色的息宁,眉头轻皱,漫步走入雨幕中,在小姑娘身前停下,温柔地朝她伸出手去,“从今往后,你名画骨,便是我太玄的徒儿了。”
“真的?”骨儿眉开眼笑,伸手搭在他温热的掌心,“多谢师父!”
太玄眯眼细细打量她,额心一点朱砂,与宁息如此相像。
恰恰,他是没有在那幅画像上点朱色的。
“画骨,你好好学,日后,自己去救你想救的人。”
小姑娘红了脸,掩面偷笑,“是,师父。”
所谓的门规,他不过是用来束缚了自己。
为了爱,离经叛道逆天而行,又有何惧?连这小姑娘都不怕。
息宁执了骨伞立在一侧,苍白的指节攀在油纸伞柄上。伞是二十四骨的,这样好的伞,却没有遇到这般好的人。
她静静地望着他们,双唇翕张终未出一言。他做的决定,她又怎阻止得了。
小姑娘爱画,又活跃得很。不出半月,玄观内满是她的作品:青墙上的木头桌子,观门上的观音菩萨,白玉地面上的朵朵墨莲,最多的,便是或飞于灌丛或栖于牡丹的蝴蝶。当然,它们都没能活过来,不然,他观中岂不是要乱成一片?
“画骨。”
她的毛笔歪歪扭扭地从地面一直蜿蜒上他垂在地上的素白衣襟时,他终于唇角抽搐地开了口。全神贯注的小姑娘被头顶的声音惊了一大跳,抬头方见身前立了个人时更是吓得跌坐在地,“师……师父。”
望见她脸上星星点点的墨迹,太玄终于忍俊不禁,“画骨,你这不是丹青,是小孩儿涂鸦。”
她又羞红了脸,攥着毛笔不好意思地问,“有什么分别吗?”
他笑而不语,俯身握住她执笔的手,顺着她刚刚画在地上的一丛乱七八糟的野花,寥寥几笔便勾出了一只墨蝶。
画骨目瞪口呆间,蝴蝶便挥动着双翼跃出地面,绕着她翩翩飞舞。
“小蝶!小蝶!”她惊喜地大喊。
这样三心二意的人,是学不好画的。息宁静静地立在殿门前,眉间好像藏着七尺冰的冷傲。
四
她是丹青师画出来的,他人的影子。她一直知道。
她更是知道,赋予她生命的那个人,总是在熟睡时眉头深锁,一声一声地唤起那个人的名字。她叫宁息。
她不需要睡觉,走路时更是悄无声息。她溜入他房间轻而易举,便每日守他床前,透过他的睡颜猜测他的悲喜,又在他醒来之前转回自己房里假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他还是潇洒清俊,不曾老去。而她更是如此,永远一个容颜,一个清冷如冰的神情。
终于有日她将手搭上他紧锁的眉,潜入他梦中。
那是一个不美丽的梦,或者说,充斥着血腥与杀戮。从混沌初开的天下大乱,到斗转星移之间的浩劫与灾难,从千年之前的烽烟四起,哀鸿遍野,再到后来解画人与丹青师的生死对决。
那一战,丹青师输了。他们惨败,面临被灭族的危险。
那个名为宁息的红衣女子,一己之私救了他。
他爱上她,本是不应该,又如此应该。
她是解画人的长老,行走时赤足,踝上系着精致小巧的红铃铛。她走向他,步步生莲,衣袂含香,周身飞舞着墨色的蝶,脚上铃铛轻轻撞击,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而后对他身后千万解画人高声说,“丹青师留此一孽,吾辈来日也好居安思危,不致过分骄傲自大。”
她看着太玄简单地擦了擦面上血迹,不动声色地笑了。
她在那女子好看的面容上,发现了自己所没有的朱砂一点。
原来,她竟还是个残缺的影子。
她放下手来,太玄正静静地看着她,一如从前那清俊的模样。她便站起来,向他欠了欠身,然后安静地转身离开。
她只是一幅画作,窥探他人梦境而不觉羞耻。可是,为什么,心却是痛的?
五
画骨随他学了月余,丹青之笔终于有了些眉目。
于是,肃穆的玄观飞满了各式各样的蝴蝶。那小姑娘像是会引蝶一般,所到之处,都是花蝶簇拥。
愣神间,一只墨蝶扑入他杯中,青色的茶水里浮出黑色墨迹,渐渐便交融了个干净。太玄单眉一挑,觉得好笑。这小徒弟的行径,真不知道该不该制止。
“师父。”画骨小姑娘委屈地撇嘴看他,“我会画蝴蝶,而且只会画蝴蝶了,可是小蝶是人啊,他清秀俊朗,笑起来可好看了。”
“画骨。”他接过息宁重新递过来的温茶,半晌才不经意地问,“我笑起来不好看吗?”
“不好看。”她有意气他,“师父有心事,笑起来自然不好看,而且,师父其实很少笑的。”
他端茶的手晃了晃,一滴青色茶水落在白衣上,晕开一点。他简单地掩了过去,更是挑起眉露出怒容,“好生倔强的小丫头。”
小姑娘一见不好,吐了吐舌头转身便跑了,留下太玄端坐在石桌前哭笑不得。
“师父。”息宁突然张了口,仍是清清浅浅,不咸不淡的嗓音,“三年了,你可曾教我什么?”
他微微一愣,竟有些心慌,“阿宁,你天资极高,不需要教的。”
“那么……”她低头想了想,继而一瞬不瞬地低眸看他,“请师父赐我一支笔吧。”
“阿宁……”太玄恍惚,竟不知作何回答。
“不行吗?”息宁轻轻地将茶盘放在石桌上,又慢慢跪了下来,“师父,求你。”
他苦涩地笑了笑,从袖中拿出一支细羊毫。她想做什么,他心知肚明。
“阿宁,你很累吗?”
“阿宁,跟我回去休息吧。”
“阿宁,不要离开。”
不远处的小姑娘忽然转了头来露出娇俏的笑,额心朱砂红得灼眼。
六
丹青师对自己的画了如指掌,因了太玄对息宁的了解,已经让他失去了对她该有的在意。
他知道她每日守在他房中,他也知道她能潜入他的梦境。所以他做了个真实的梦,梦里天翻地覆,让人心慌。
他让她看见了自己的死。
艳色的红衣女子目光逐渐变得空洞,姣好的面容消散在风中。宁息滥用长老职权寻个借口放过了他,最终遭到族人诛杀。
她脚踝上的红铃铛,摄魂夺魄,也能魅惑人心。但人总会醒,生命无比长的神仙,总不会一直被困在一个如儿戏般的谎言里。
息宁执笔在自己身前划,虚空中笔走龙蛇,透过飞舞的羊毫笔,他看到她目光沉寂安详,一如往昔,一如这三年的点点滴滴。太玄的心突然有些痛了,他本以为,自己厌了,对丹青,是如此的厌了。
息宁的脚下逐渐蜿蜒出浅淡的墨色水渍,那水渍,慢慢地往上翻腾,一点一点地,最终消融了她的全身。
他才发现,她也从来赤足。
他不由自主地伸了手去,却什么也没抓住了。
“师父。”画骨小跑过来,嬉笑着抬头看他,朝他伸出沾了墨的手,“坏姐姐,死了呢。”
她的小手很自然地搭在太玄滞在空中的手上,恍惚间好像回到了那日落雨的午后。
太玄征了征,却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直直质问出声,“解画人,你为何要学画。”
“为何要害我。”
七
“阿玄,我怎么会害你?”小姑娘眉眼弯弯,一脸无辜。
阿玄。
时光好像一瞬穿梭了千年。
那时候的宁息低头看他,三千青丝柔柔地倾泻下来,擦过他的额际,灼灼红衣迷了他的眼。
那时候的他狼狈得只能匐在地上喘气,却仍是倔强地擦干净脸上的血迹,狠狠啐了她一口。
她笑着,立在他身前,轻描淡写地,为他抵挡了身后千军万马。
“阿玄,以后啊,你就是我的人了。”
她如是说。
太玄看着眼前小姑娘逐渐长大的身形,突然明白了一切。
“小蝶,我的红铃铛,呐呐,看呐,他回来了。”画骨另一只手拎着刚刚画出来的铃铛,得意地伸在他眼前晃。
所以因此学画吗?
“阿玄啊,你抽了我一丝魂魄注入画中,可是害了我找得辛苦啊。”
“你看,我还总长不大呢。”
所以息宁……早就知道了是吗?
她的身形逐渐回到千年前的那个样子,三千青丝挽于耳际,眉眼间清浅笑意,一袭红衣灼灼芳华。
她的手依然牵着他,周身还萦绕着飞舞的墨蝶。又向他走近些,踝上缠着红铃铛,足下生莲,每一步都踏出繁华万千。
她经历了什么才能活过来,好像已经不重要了。她依然是那个风姿绰约睥睨众生的解画人长老,也是那个俏皮顽固的蝶仙。
息宁在她身上,得到了永生。
太玄一下便释然了。
眼前的人曾经是如此魂牵梦萦,千转百回。他终于舒眉笑起来,“宁息,你回来了。”
“对呀。”她也抬头笑迎,眉心朱砂一点,煞是好看,“阿玄,对弈吧。”
可现在,掌心的温度是如此真实,真实得让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丹青师太玄,笑着潸然泪下,声音沙哑。
“等你三年了。”
手里的人儿点点头,俏皮眨眼,“不过,我叫画骨,有个笑起来极其难看的师父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