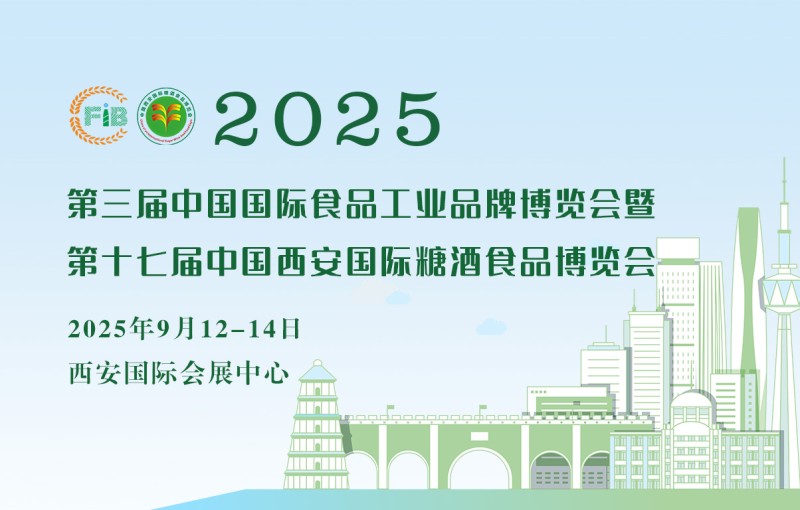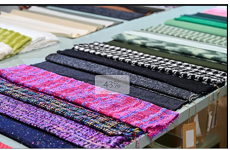注:本篇评论中除引文外,所有的“她”都指作者本人,特意规避了用“她”来代指除作者本人以外的任何人。
本是想读完邱妙津的两本再一同评论的,但是看的过程中,有一种冲动促使我想对《蒙马特遗书》中的特定内容进行记录和评论,那么就破成两篇文章来写吧,这一篇更微观,另一篇更宏观。本文是阅读《蒙马特遗书》中随想随记的札记,记录一些文本细节与自己的即时思考。
第三书:她爱着絮,这是感性领域,理性领域她知道她爱着一个已经不值得她爱,也不值得她尊敬的人,毕竟絮已经是如此地背叛了她。
它不会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却会是一个年轻人在生命某个“很小的部门”上深邃、高密度的挖掘,一部很纯粹的作品。——《蒙马特遗书》第五书
艺术家死后方才伟大,而伟大的艺术家往往都有如此的自知之明。
第六书:一个和她对等的人(清津)的示爱被她暂时压下、暂时拒绝。
前九书读完:我觉得她对絮的爱是唯心的(不过爱当然总是唯心的)。被絮玷污却仍然非理性地爱着絮。
个人认为,《鳄鱼手记》中她与水伶的那一段她后来自觉不够成熟的经历让她产生了补偿心理,才会导致絮如此背叛她、如此不适合她,她仍在爱着絮。这种补偿心理具体是:她曾经不相信水伶爱着她导致她逃离水伶,但后来发现水伶不但爱着她,而且出于无法直面她离去的事实甚至内心构筑了一个她继续爱着,她的归来使得水伶内心的她,和现实的她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混乱,此时浪子回头已经晚了。这确乎成了她原生家庭一般的创伤,要在她未来的人生中反复上演。面对絮时,情景一样只是身份互换了,絮成了当初那个犯了错的自己,而她成了当年的水伶,现在的她目睹着絮和她当年一样犯了错,她也要像水伶一样坚持爱着絮等待絮像当年的她自己一样因为走向成熟,构建了更为自洽的体系而回心转意,重新爱她。她曾经深重地辜负了水伶,现在轮到絮深重地辜负她了,这大概就是轮回的命运,是悲剧性。
第七书中提到的“怪”和第九书中提到了“因为我的‘不被满足’而被抛弃”:所谓的“怪”在我理解其实就是pua、价值灌输,就是通过“怪”来要求对方,促使对方改变以满足自己,而作者又说“永在性”最为重要(第九书),这是一个浅显的矛盾,作者对絮或者说对她另一半的要求太高了,以至于另一半终于无法忍受作者的“怪”、作者的pua、作者的不满足,只能打破“永在性”丢下她逃走了。
我要特别插一句,pua这个词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使用它的过程中,我将它理解为一个中性的,尚未被污名化的词,因为爱都是自私的,在爱的关系中,每个人都希望对方做出改变来符合自己心目中幻想出来的对方的形象,不存在一对不需要任何改变就能完美适配对方的情侣,因此争斗、互相改变和磨合大概也是一段亲密关系中必然具备的要素,而pua只是表达自己需求的一种手段罢了。
“怪”成了逼迫对方打破“永在性”的根因,如果“永在性”真的如作者说得这么重要的话,又为什么要用“怪”给对方这么大压力呢。其实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在爱什么”,无非是爱唯心的幻象,需要永在的是心中那个完美的幻象,因此才不可能,而“怪”就来源于唯心的幻象和现实的人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当被爱的人(絮)意识到自己无法和作者唯心的幻象合一时,絮只能打破幻象,打破永在性逃走。
我正是因为这样的“不被满足”而一度地使水遥选择不要我,而跟另外一个人走;二度地又使立誓要全心全身地满足我的絮,后来也顾不了我会面临什么样恐怖的灾难,而以最悲惨的方式硬生生地背弃我。——《蒙马特遗书》第九书
水遥即水伶,前文分析作者和水伶的经历导致作者原生创伤的时候提到原因是:她不相信水伶爱她,引文中作者将其归结为“不被满足”,是自洽的、同义的。在作者看来,水伶没有付出足够令作者相信水伶在爱着她的那么多爱,所以她逃走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后续对絮的行为,其实就是在试图弥补和水伶的遗憾。和水伶,她因为得不到满足而逃走了,这次她不逃走了,要试图让对方改变来满足她,结果把对方(絮)逼得逃走了,悲剧性再次显现,仿佛一切都在轮回。
第十二书中,“自杀”一词已经频繁出现,这是之前行文中都不曾有的,作者理性分析了自杀之于她的意义,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自杀宣言。
第二份第十七书,讲作者去东京和小咏的经历。
作为体验一个人的心,不听其言只观其行,这种特殊的原则,用在她这种特殊的人身上,绝对是没错的,这也是我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才学会的。 ——《蒙马特遗书》第二份第十七书 (注:该引文中的“她”指小咏)
作者评论小咏刀子嘴豆腐心,留学日本的小咏,性格和行为方式上十分地受了日本文化浸润,或者不如说是我们东亚文化一贯是如此地内敛和持守。本书中两章“第十七书”,均是写小咏的,可见小咏在她心中地位之重。
我想与她一起活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分钟,我只想见到她,只有她能给我欲望,给我勇气活下去,我只会想为她活下去,因为只有她的生命是真正需要我,需要我活着的,我会想要活在那儿给她看,给她信心,给她勇气,我想活下来照顾她…… ——《蒙马特遗书》第二份第十七书 (注:该引文中的“她”指小咏)
阅读至此不禁感叹,之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能达到引文中地位的人必然是被作者所爱着的吧,我并不是否认作者对小咏的爱,我的观点在于,承担这个责任的角色本应是絮的,在作者的理性中絮已经是如此地失格,如此地将作者推向死亡,以至于造成了如此的错位情景:在小咏成为了作者活着的凭依,甚至是最后的稻草之时,在作者心中爱的殿堂中放着的,仍然是絮。我当然没有资格说我理解或是感同身受作者的痛苦,但我猜想在理性上已形成了如此错位的她,得是承受了多大的痛苦。而这最后的稻草小咏,这断简残篇真的唤起她生的意志吗?
赖香吟在纪录片《蒙马特的爱与死》(2019年陈耀成所摄纪录片)中提到了赖的心目中,邱妙津创作《蒙马特遗书》是为了生,而不是外界普遍认为的自杀宣言。我是非常同意赖的观点的,我只是一个读者,并非局中人,更完全没有一丁点资格和小咏比谁更了解邱妙津,我只是想说说我关于此的思考。生和死,或者说选择活下去还是选择自戕,从结果表现上来说只能表现为一种,因此成为两个鲜明的极端,但是生的意志和死的意志,在邱身上是同时辩证存在的,而艺术创作这种理性实践毫无疑问是邱生的意志的体现,因此我十分同意赖香吟对于《蒙马特遗书》是邱生的努力和尝试这一观点的。但死的意志在邱身上也是确实存在的:长期抑郁(厌食和失眠无疑都是她抑郁的躯体化表现),自残行为。邱最终自戕的结局,是她身上的死的意志压倒了生的意志的结果。而十分可悲的是,理性在这两种意志交缠斗争中往往只能处于无助,甚至是将死亡正当化的境地,请看如下引文:
絮常笑我是恐怖分子加神秘主义者,我是吗?我能不是吗?之于人类生存之中非理性和超自然的界域,我真的能有所选择吗?理性,真的可以拦住一个人使他不要死亡不要发疯,真的可以拦住一个人不要任意对所爱的人不忠,或是可以使人不在瞬间被不忠的雷电劈死吗?我很绝望,尽管到最后一天,这些答案对我还是No…… ——《蒙马特遗书》第二十书
我并不是为了要惩罚任何人,我并不是为了要抗议任何罪恶。我决定要自杀,以前所未有的清醒、理智、决心与轻松,是为了追求关于我生命终极的意义,是为了彻底负起我所领悟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的责任……我对我的生命意义是真正诚实与负责的,尽管我的肉体死了,形式的生命结束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的灵魂就因此被消灭,无形的生命就因此而终止。只要我在此世总结是爱人爱够,爱生命爱够了,我才会真正隐没进“无”里,如果在这个节点,我必须以死亡的方式来表达我对生命的热爱,那么我还是爱不够她,爱不够生命的,那之后,我必须还会回到某种形式之中与她相爱,与生命相关……所以肉体的死亡一点也不代表什么,一点也结束不了什么的。 ——《蒙马特遗书》第十二书
我想如今的书写行为是最后一场试着宽恕絮的努力,如果连这最后宽恕她的努力也失败,我也不可能活在一个如此深恨她的躯体里,我必将死,死于一场最后的和解行动,与我的生命,与我最深的爱恨纠结和解,这也是能与她的生命和解的最后方式…… ——《蒙马特遗书》第九书
可以看到理性在生死意志的交缠中,恐怕甚至是站到助长死之意志的阵营中去了,当理性处于那个位置,剩下的恐怕只有一个导火索触及邱的感性,最终她自戕悲剧的发生也是可以预料的了。这个导火索正是絮的到来。如作者所说,在这场死中,她与她最深的爱恨纠缠和解……
无论是读《蒙马特遗书》,还是写这篇评论的时候,我都不得不因被她的浓烈触动而常常停下来平复情绪和止不住地叹息。浓烈纯粹的她离去了,只剩下善于平复自己情绪的庸才们仍蝇营狗苟于世,在她离去后丑陋地拾其牙慧,书写着平淡干瘪得没有任何意义的文字,而她已离去,她已离去。
她朝着她的永恒,一往无前地奔去。